来源:北京社会科学

文化折叠:中国“学二代”家庭
代际文化的传递与冲突
摘 要
“学二代”在中国社会情境中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也是中国新中产群体的一个缩影。作为家庭文化资本的继承者,他们由于良好的家庭教养和充实的物质资本而被认为是安全而充满优势的一代。但现实中“学二代”的生存图式并非一味趋同或呈现文化符应,而是形成了不同的生活图景。研究选取14组“学二代”家庭进行长达一年的民族志研究,在“学二代”循规顺应、吃力维持或冲撞逃离的自我呈现背后,看到了家庭代际文化传递过程的“文化折叠”。正是“两代人”在社会经历的场域、资本和惯习方面的文化重合及外延性差异,形成了现代社会中“学二代”家庭代际文化传递过程的交织与冲突。
但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学二代”是一个综合而又复杂的结合体,他们在教育与成长过程中,既受到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影响,又受到后现代意识的文化冲击,同时还保留着父辈从乡土迁移到城市过程的文化痕迹。所以,他们身上叠印着父母的惯习性情,也融合着后现代城市青年的习性。因此,在社会现实中我们也看到“学二代”的生活图景并非一味趋同和实现文化符应,而是呈现复杂性和多元性。
一、“学二代”在家庭代际文化中的自我呈现
二、文化折叠:“两代人”的教育对话与反思
(一)文化场域折叠——从乡村到城市的迁移在中国社会情境下,“学一代”是现代性社会中“半乡村半城市化”的综合体。他们的基础教育始于乡土情境,源自一种由童谣、乡俗、族规等组成的淳朴的乡土文化。“学一代”的刻苦努力带领了整个家族文化阶层的流动,文化场域也从乡土完全迁移到城市。但由于乡土情境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文化是稳定的,更倾向于在悠长的时间中,从容地去摸熟每个人的生活。因此,“学一代”的情感状态是一种先验的羞涩与敞开,在城市生活中面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时,他们既表现严厉又想做到民主,既不善于表达又渴望与孩子沟通。
当“学一代”和“学二代”在城市场域相遇,并以家庭为单位共同生活时,“学二代”已是完全的“城市化”产儿。他们在城市文化中习得开放、多元、自由选择的惯习,也在快速传播和接受信息中建构着社会网络关系。他们维持着虚拟空间的社交亲密,也在现实生活中保持着城市人的疏离。因此,相对于父辈的羞涩与敞开,他们更善于隐藏自己的情感,也更善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其父母常常不了解孩子在想什么,仿佛彼此之间隔着一道隐性的“门”。因此,文化场域迁移背后是城乡文化的折叠,更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交织和碰撞。
(二)文化资本折叠—— 一种“成全文化背后
对于阶层群体自身文化差异的解释,威利斯认为“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层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我们从“成全”一词看到了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成全”是帮助他人实现自身愿望的活动;是一种跳脱于个人之外的社会助推力;是一种他者顺应主体意愿帮其成就事物的过程。但事实上,在社会现实中这种“成全文化”背后存在着双面性。一面是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成全”,另一面是违背主体意愿的“被成全”。中国“学二代”家庭两代人的文化折叠恰是以文化资本为载体的“成全”与“被成全”关系。
中国社会情境下的“学一代”是村落家族中考入大学的第一代人,他们背负着祖辈“走出去”的期望,也承载了实现家庭文化阶层上升的重任。即使在城市扎稳脚跟,在城市生活和社交中依然存在着紧张感和局促感。正因如此,“学一代”希望用自己的理性文化带给其子女隐性的优势,试图为“二代”铺陈一条平坦且宽广的“成全”之路。但相对于“学一代”从无到有的文化资本创生历程,“学二代”从出生之始便浸润在父母的 “成全”文化之中。父母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亲子关系,子女关于学习的一切要求似乎都可以得到满足。但同时父母的城市焦虑也渗透进“学二代”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为子女精心提供各种额外条件,每一项都像是一道标签,似乎只有加持在身才能更胜一筹。这套教养文化的逻辑貌似建立在自由民主的理念之上,却又不得不包裹着现实竞争压力的外衣。年轻一代对于“成全”抱有一种选择性态度,认为“成全文化”潜隐着“被成全”的规训和权力的束缚。因此,倾尽所能的“成全文化”在“学二代”身上并不一定完全奏效,反而拉紧了亲子之间的弦。
(三)文化惯习折叠——“子承父业”还是“另辟蹊径”无论是文化场域还是场域中的资本形式,都以一种性情和惯习的方式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费孝通认为,乡土社会中最主要的惯习是存在“孝”的特性。这也就不难理解,“学一代”被称为“懂事”的孩子。因此,“使父母过上好日子”“走出去看外边的世界”“不想让自己的下一代受苦”,这些意向承载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情感,在“学一代”的人生经历中一以贯之。相较而言,在新型媒体所传递的经验背景下,“敢于试误”和“寻求自我认同”成了“学二代”年轻人最鲜明的特点。他们在日常生活琐事的决策和在自我认同的呈现,都在回答“我将如何更好的生活”。因此,对于“学二代”而言,父辈的文化资本给予了他们可以多元选择的机会。也给了他们产生新的文化理解,建构新的文化情境的可能性。
原载《北京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有删减。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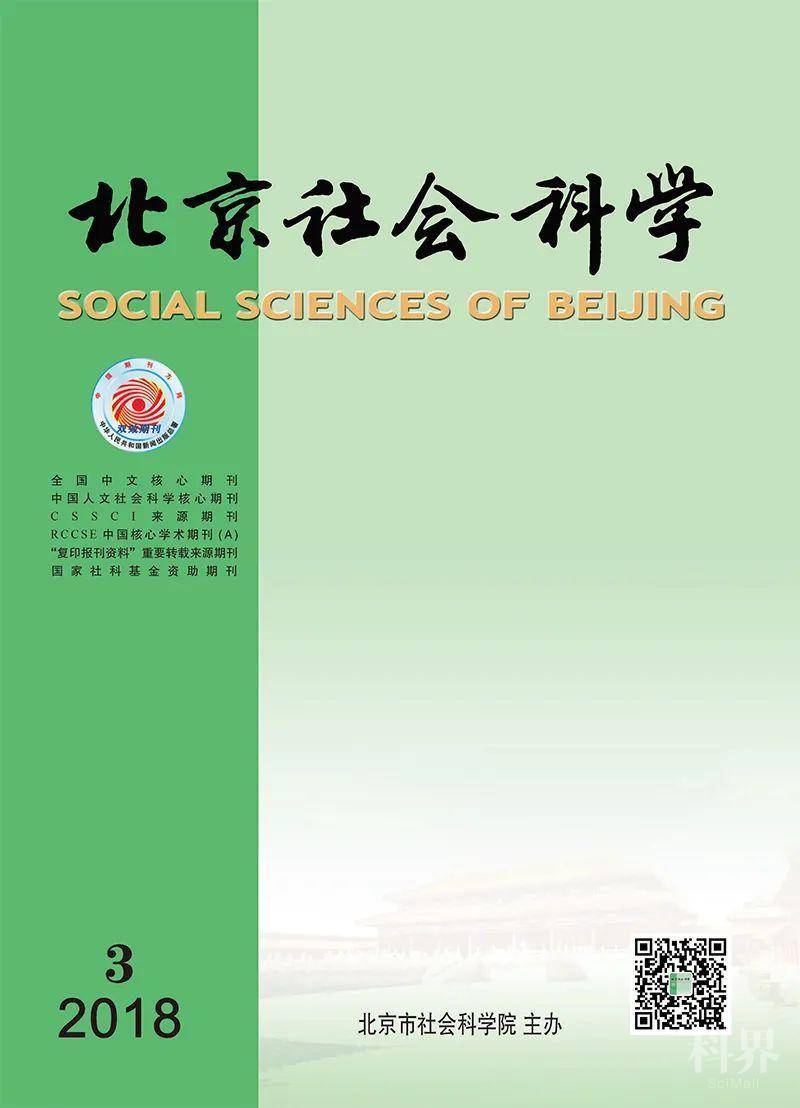
来源:bjshkx 北京社会科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xODM4NTgxOQ==&mid=2247486522&idx=2&sn=6c68441432f43e00588c37c2529dfec2&chksm=97ea10cea09d99d83b9bbdc6b10a5cbab0f265c766f1a877d18b898f7144a73e1c15e69fe53c#rd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注明,本站所载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参考、交流、公益传播之目的。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电话:(010)86409582
邮箱:kejie@scimall.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