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土地科学
《土地科学动态》2020年第3期重点关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相关重大问题”,主要议题包括:《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与土地征收制度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落实、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制度构建和其他重大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编辑部联合郑州大学中国土地法研究中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土地法制研究院、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土地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采用腾讯会议辅以同步直播的形式组织专家研讨,形成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文章,现通过本微信公众号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通过《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具体细化
“公共利益需要”
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 李 平
多年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征收法律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公共利益需要”没有法律界定。自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以来,经过十年磨剑,终于在新《土地管理法》中得以体现。新法以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需要”范围,但要真正实现其立法意图,还需要包括《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在内的配套法律法规细化规范和填空补缺,让列举的“公共利益需要”切实可行。以下是笔者的思考与建议。
一、“成片开发”的完善
新法第45条以列举方式界定公共利益,无疑是修法的最大亮点之一,但该条第一款第5项将征收集体土地用于成片开发界定为公共利益,也是这一修法亮点中的最大瑕疵。尽管针对成片开发加上了符合各类长远规划、经济发展年度计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开发标准等限制性条件,但毫无疑问的是,成片开发条款并未详细说明这种开发建设的内容,甚至也没有为进一步界定提供任何指导。在定义缺失的情况下,该条款有可能使地方政府绕开公益目录限制,通过调整规划扩大城镇区域而征收目标地块。
中国的城镇化势必要将适宜城镇化的集体农地成片开发为城市建设用地,而大多数城镇化设施,如住房、写字楼和餐饮商场等,都属商业性质,为商业设施征收土地很难说是为了公共利益。虽然这些商业性质的城镇化建设很有必要,但将之列入“公共利益需要”目录,会严重影响公益征地法律的完整性,难免为人诟病。另外,为城镇化服务的成片开发土地一般位于城郊或政府准备建设的新城,其地价远非区片综合地价可以比拟。如果按常规的征地处置,势必引起农民的强势反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城镇化建设不能像印度、巴西那样杂乱无章,城镇化与贫民窟并行。有序的城镇化建设必然仰仗精心规划的成片开发;若不依靠政府征地,则须挨家挨户告知目标地块的产权人,进行逐户谈判。一般而言,这种过程漫长而繁琐,交易成本巨大。更糟糕的是产权人若不出让,无论所涉地块多么小,最终都会破坏整个城镇化项目的实施。因此,必须在推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利益和农民的土地产权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在最大限度保护农民利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赋予政府有限的城镇化征地权力。
值得庆幸的是,《土地管理法》第45条把成片开发纳入公共利益需要的同时,又特别要求成片开发必须符合“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这一上位法的要求实质上等于是授权包括实施条例在内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进一步细化成片开发的规范。基于征地制度改革的中央政策和《土地管理法》的修法意图,按利益平衡思路在实施条例中细化成片开发必须遵循的规范。如何细化?中国台湾的区段征收制度值得借鉴。
与中国大陆一样,台湾也是以列举方式定义公共利益。在这些列举的公共利益之后,台湾也是将为城镇化建设的征收视作公共利益。对这类事实上含有经营性目的的城镇化征收,大陆叫“成片开发”,台湾叫“区段征收”。在台湾,纯公共利益征收的补偿是农地的农用市价,类似于大陆的区片综合地价,程序要求也相对较低。但是,对“区段征收”,补偿标准不再是农地的农用市价,而是相当于被征农地总量40%-50%,但已转为高市值建设用地的所谓“抵价地”。除公共利益征收的常规程序之外,“区段征收”还要求政府必须先行尝试购买目标土地,购买不成方可启动“区段征收”,而且即便启动,除反复听证沟通而外,还需要绝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同意。台湾的做法,显然是在“关门”和“开窗”之间维持一种平衡:既然开启政府非公益目的征地之“窗”,那就得关上低门槛公益征地之“门”。对农民也是一样:既然关上“非公益不得征地”之“门”,那也就应该开启提高补偿强化程序之“窗”。台北到高雄的高铁征地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范例。台北—高雄的高铁2007年建成通车,其线路用地采用公益征收,而沿线的五个新车站用地则采用区段征收。尽管车站用地也可以通过公益征收取得,但公益征收的土地只能用于车站建设。政府意识到,建一个高铁站往往带来一个新城区的兴起,需要统一规划,而新城区建设必然包括各种商业用地。高铁沿线五个车站的属地县政府区段征收了670公顷私人农地。虽然补偿是被征面积40%的抵扣地,但由于规划用途上调,其价值比100%农地的农用价值高出10倍以上。60%的土地被政府无偿取得,其中大部分用于公益建设,如车站、道路、学校、公园等,小部分出让给开发商,出让金则用来建设公益设施。其结果是政府和农民双赢:政府不花一分钱白捡一个围绕车站发展起来的新城区,农民也由于地价上涨而财产大幅度增值。在征地制度改革过程中,中央反复强调要提高农民的获得感,让农民分享城镇化的红利。在实施条例中对成片开发的补偿和程序制定一套相应的标准,既是落实中央指示精神,也符合《土地管理法》要求。基于以上分析,建议实施条例加上一条专为成片开发设置的标准: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组织实施成片开发建设需要依法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应分别征得至少百分之八十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并允许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选择区片综合地价货币补偿或不低于被征土地面积百分之四十的建设用地留地安置。二、土地储备与土地征收土地储备源自西方国家,是政府通过市场手段收储因各种原因而闲置废弃或利用低下的私人土地,经过重新规划、整治或重新开发后再投入市场,实现政府的土地利用目标。尽管不同国家实施土地储备的初衷各有不同,但所有这些国家的土地储备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通过市场渠道收购土地。中国土地储备制度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其初衷是为了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建立专门机构收储经营不善、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持有的划拨土地使用权。但随着国企改革的完成,各地土地储备机构的收储对象包括了通过农地征收获得的土地。目前,全国各土地储备机构收储的土地通过政府征收的农地占了较大比例。如:安徽征收农地在整个土地储备的比例为90%,重庆为80%,其他省市自治区都在50%以上。《实施条例》草案第19条认可这一土地储备制度。根据2018年颁布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土地储备是国家“依法取得土地,组织前期开发、储存以备供应的行为”。简言之,土地储备就是“拿地、开发、卖地”。为让土地储备适用于农地征收,该办法又将征收的集体土地也纳入土地储备范围。也就是说,如果储备对象是集体土地,那就是“征地、开发、卖地”。这一三段式的行为清楚表明,就土地储备型征地而言,作为征收方的土地储备机构在征地之日并不知道被征土地是否使用于公益目的。从各地收储机构的具体操作来看,出于储备土地需要的征地,大多没有具体项目的支撑;征收土地的目的,是在补偿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先行征收储备土地,以待日后地价上涨再投放市场。在2019年新《土地管理法》通过之前,这样的土地储备运作也许还无可厚非,因为法律没有界定“公共利益需要”;把政府收储土地认定为“公共利益需要”也不能说完全站不住脚。但是,现在不同了。新《土地管理法》第45条以列举方式界定了征地范围,并不涵盖土地储备。另外,第45条第一款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有下列情形之一,确需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可以依法实施征收”。在这里,法律强调了“有下列情形之一”和“确需”等,其立法意图非常明显:征收农民集体土地时,公益目的必须明确、具体,而且还确有必要。为了土地储备的征收既无具体的公益目的,当然也就无法证明确实需要动用征收这一政府权力。显然,条例草案第19条如果成为法规,操作起来势必与其上位法——《土地管理法》形成冲突。土地储备是一专项土地制度,其地位应该与土地调查制度、土地统计制度和土地登记制度平等,由全国人大通过的《土地管理法》认可,而不是借行政法规来确立身份。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新《土地管理法》一一列举国家认可的专项土地制度:土地调查制度(第26条)、土地统计制度(第28条)、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第4条)、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第33条)等。耐人寻味的是,《土地管理法》完全没有提及土地储备制度,这似乎意味着立法者对土地储备制度的合法性心存疑虑。在上位法只字不提的情况下由行政法规来认可,有越位之嫌。有鉴于此,建议删除第19条。
三、双重用途征收
《土地管理法》第45条禁止政府为了经营性用途而进行土地征收,非常必要。但是我们同样也要认识到,征收土地的用途有时可能是公益性和经营性兼而有之。比如,建设高速公路显然属于公益性,在第45条的列举范围之内,征地无可厚非。但是,兴建高速公路还必须考虑服务区建设,如餐馆、加油站和超市等,而这些用途又明显属于经营性。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办法是一刀切:高速路用地通过征收解决,服务区用地由使用人通过市场购取。这种方法的好处是保障了只能因公益需要征地的法律完整性和严肃性,但其弊端也同样明显:公路建设必然导致地价飞涨,难以避免服务区用地的权属人坐地起价。按市价成交又有可能反过来影响线路用地的权属人,要求征地补偿一视同仁。而且,市场交易必须建立在完全自愿基础上;如果一个权属人不愿出售,服务区选点就必然泡汤。为平衡法律原则与实施效率,建议对双重用途的征地进行三方面考量:第一,项目用地的经营性用途无法独立存在,必须依附于项目的公益性用途才能发挥作用;第二,要实现项目的公益性目标,经营性用途必不可少,是项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在整个项目中经营性用地发挥的作用是次要的辅助性和支持性作用。如果双重用途性征地中的非公益性用地满足这三方面要求,便可视为公益性用地,按征收处理。为此,建议条例增加一条:县(市)人民政府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进行的土地征收同时具有该条列举的公益性用途和没有列举的非公益性用途的,其非公益性用途必须依附公益性用途而存在,为实现公益性用途所必不可少,属于次要和辅助性用途。声明:本文为原创作品,版权归属于《中国土地科学》编辑部,纸媒、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转载请注明出处,对于不注明出处的侵权行为,本刊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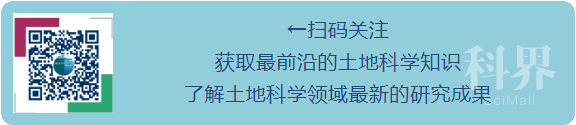
(本文责编:孟 鹏;网络编辑:曾 爽)
来源:gh_c372e50c8789 中国土地科学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1NTM4MzMzOA==&mid=2247485578&idx=1&sn=2bdebe703c6a48442c0078d8b862e3d2&chksm=fbd467cfcca3eed9da5b0a12b5f8853b1b5f064981d19709db4a0b1503d817bc51339b52139c#rd
版权声明:除非特别注明,本站所载内容来源于互联网、微信公众号等公开渠道,不代表本站观点,仅供参考、交流、公益传播之目的。转载的稿件版权归原作者或机构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电话:(010)86409582
邮箱:kejie@scimall.org.cn